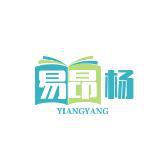20世纪40年代的尼日利亚,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

一群本土艺术家却开始在殖民文化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声音。
当时前往伦敦斯莱德艺术学院深造的本·恩沃乌,在导师亨利·摩尔的工作室里第一次意识到:非洲传统雕塑与欧洲现代主义竟有如此多共通之处。
这位1917年出生于奥尼查的伊博族艺术家,后来成为首位获得全球认可的非洲现代主义者。
尼日利亚独立(1960年)成为艺术爆发的催化剂。
与传统认知不同,尼日利亚现代主义并非欧洲艺术的简单复制。
加州大学艺术史教授西尔维斯特·奥克沃诺杜·奥格贝奇指出:“恩沃乌的作品融合了伊博族假面舞会文化与古典训练,就像把两种不同的基因嫁接在一起,结出了全新的果实”。

这种融合在技术上体现为乌里(uli)传统技法与现代构成的结合:伊博族妇女用在身体上绘制的螺旋纹样,通过艺术家的转化成为画布上的负空间构图。
更令人惊讶的是尼日利亚女性艺术家的早慧。
陶艺家拉迪·夸利将瓜里族传统的蜥蜴、鱼纹样刻在现代陶器上,她的肖像如今被印在20奈拉纸币上,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

伦敦邦瀚斯拍卖行的非洲艺术专家海伦·洛夫-阿洛蒂分析:“夸利的意义在于证明了现代性不必以抛弃传统为代价,她姑姑教的手工缠绕技法,与伦敦的陶艺训练同样重要”。
流散与回归:移民艺术家的双重困境
乌佐·埃戈努的《无国籍人士》系列创作于1981年,但其中蕴含的漂泊感却贯穿了他的一生。
这位在20世纪40年代就定居伦敦的艺术家,比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更早体会到文化身份的多重性。
他的画作中经常出现贝雷帽、行李箱、地图等符号,如同一个永不停歇的文化翻译者。

这种流散体验催生了独特的创作方法论。
埃戈努曾自述:“我的调色板上有两个太阳,一个是尼日利亚的烈日,另一个是伦敦的薄阳”。
在他的作品中,伊博传统的强烈色彩与英伦的灰调形成了微妙平衡,正如艺术评论家所形容的“在两种文化光谱间走钢丝”。
更复杂的案例来自恩沃乌。
1957年他受委托创作伊丽莎白二世雕像时,正处于殖民与后殖民的转折点。
奥格贝奇教授揭示了这个悖论:“他为英国女王雕塑的同时,也在家乡创作伊博族祖先雕像。这种双重性不是分裂,而是现代非洲艺术家的真实处境”。
值得注意的是,恩沃乌始终坚持使用父亲传授的传统雕刻工具,即使面对最经典的欧洲大理石时也不例外。

被低估的市场价值:从边缘到主商业化的长征
2018年,恩沃乌的画作《芭蕾舞裙》以167万美元成交,打破了非洲现代艺术的市场纪录。
这个数字在西方现代主义大师面前或许微不足道,但对非洲艺术史而言却意味着价值重估的开始。
邦瀚斯拍卖行的数据表明,2023年拉迪·夸利及其阿布贾陶艺培训中心女性同行的作品拍卖成绩,较五年前增长了300%。
市场觉醒的背后是学术研究数十年的铺垫。

奥格贝奇2008年出版的《本·恩沃乌:一位非洲现代主义者的诞生》首次系统梳理了这位艺术家的创作脉络。
与此同时,Instagram账号“非洲艺术史”通过社交媒体将散落世界的非洲艺术作品重新连接,其运营者海伦·洛夫-阿洛蒂指出:
“年轻收藏家对文化多元性的重视,正在改变艺术市场的权力结构”。
2025年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尼日利亚现代主义”大展,更像是一场迟来的正名。
策展人奥塞·邦苏直言:“我们习惯将现代主义与欧洲艺术史捆绑,事实上它是在多种语境中并行发展的”。
展览中的250余件作品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从殖民时期到后独立时代的完整谱系。

包括那些曾被归入“民俗艺术”的乌里纹样,如今终于在与蒙德里安网格对话的展墙上获得了平等地位。
重构现代主义:全球南方视角的艺术史重写
泰特展览的颠覆性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为什么皮特·蒙德里安的几何抽象被视为现代主义经典,而同样运用几何秩序的乌里纹样却长期被排除在现代艺术叙事之外?

皮特·蒙德里安
策展团队通过并置展示给出了答案:这两种发源于不同文化的视觉系统,其实都在探索点、线、面的本质力量。
这种重构不仅发生在美术馆领域。
2025年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黑色巴黎”展览、纽约福特基金会画廊的“人体陶土”展,不约而同地将非洲艺术家的贡献纳入现代主义谱系。

其中夸利的陶器与卢卡斯·萨马拉斯的新造型主义作品并列展出,暗示着现代性本应有更多元的表达方式。
更深层的变革在教育领域酝酿。
策展人邦苏透露,泰特正在与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合作数字化档案,那些曾被殖民者带走的文物将以数据形式“回归”。
他认为:“当人们看到恩沃乌在1949年创作的《市场场景》与同时期欧洲抽象表现主义的相似性时,就会理解现代主义从来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的”。
结语:未完成的现代性
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出口处, visitors会看到拉迪·夸利1965年的陶罐《水之记忆》。
容器上的蜥蜴纹样游动在德国釉料与非洲黏土之间,像极了尼日利亚现代主义的隐喻:
它既不属于纯粹的传统,也不是西方的仿制品,而是在碰撞中生成的第三种语言。
当乌佐·埃戈努画中那个戴贝雷帽的身影,终于从展览画册走进艺术史教科书,这场持续了80年的现代主义叙事革命才刚刚开始。
正如奥格贝奇教授所言:“问题的关键不是让非洲艺术进入西方殿堂,而是重新思考,究竟谁有资格定义什么是现代?”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曾被视为“边缘”的创作里:
恩沃乌面具中凝视未来的眼睛,夸利陶器上永不停游的蜥蜴,以及埃戈努画笔下那个永远在行走的无国籍者。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上海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