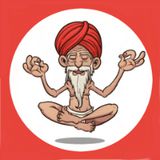本文共计:3826字,11图
阅读预计:10分钟
笔者曾前后旅居印度4年——每每遇到新认识的印度朋友时,除了“Haan ji,mujhe Hindi aati hai”(是的,我懂印地语)之外,这是我拉近关系的最直截了当且切实有效的话术,没有之一。
一听到这句话印度朋友一般都会接着问:“你在印度时会出去旅游吗?”当获得肯定的答案后,他们总会一脸自豪和期待地追问“都去过哪些地方?”
每当这时,我就会如数家珍般把自己去过的地方罗列一遍,满足他们溢于言表的民族自豪感。
孟买,德里,阿格拉,那格浦尔,斋普尔,乌代普尔,杰伊瑟尔梅尔,焦特普尔,斯利那加……
但每每提起来又总会想到离开印度后的三大遗憾:恒河,喀拉拉,还有春天的克什米尔。这是我始终心心念念、求而不得的三个地方。
人间仙境喀拉拉邦
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喀拉拉邦,以“最不像印度的地区”闻名于世,BBC称其为“印度最美的地方”之一,《国家地理》将其评选为“十大旅游天堂”。
每年季风季,当西南季风翻越西高止山脉并席卷全印度时,它浸湿了植被,使其笼罩在难以想象的绿荫中。
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雨中的喀拉拉邦一样,提供一种冥想的平静和神奇的治愈感。根据阿育吠陀的说法,这是自然和人类补充和恢复活力的最佳季节。
同样也是这个季节,在生机的背后也让喀拉拉邦这样一个人间仙境,屡屡陷入死境。
想象一下,如果德里一年的降水量集中在短短48小时内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泻在一片本就已为季风季的暴雨浸透了的小山坡上,将是什么样的场景?
当人们脚下的土地最终崩塌时,位于喀拉拉邦西南部的Wayanad地区的两个村庄也在一片死寂的深夜里永远地陷入了死寂。
灾难前的Wayanad村庄
天灾还是人祸?
7月30日,Mundakkai与下游两英里处的Chooralmala两个村庄结束了它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噩梦——可怕的泥石流、洪水和死亡。
回顾一下灾难发生的始末,让我们不禁发出疑问: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7月28日-29日,暴雨袭击了Wayanad地区,Meppadi县最靠近Mundakkai村的雨量计记录了48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了572mm;
7月30日00:45,暴雨引发了Vellarimala山的山体滑坡,淤泥、碎石、被连根拔起的树木滚滚而来,冲到了坡下3.5km处的Mundakkai村,从海拔2000m高的山坡倾泻而下的泥石流,像溃坝一般几乎冲走了整个村落;
7月30日4:10,接踵而至的第二次山体滑坡又一次袭击了Mundakkai村,同样也冲走了2.6km以外的Chooralmala村,连接两个村庄的桥梁被冲毁,救援行动受阻;
7月30日5:30,在Malappuram地区河流下游约12km,距离公路90km的地方,发现了人体残肢,不久后又接连搜寻到64具遗体。
截至7月31日晚,已有230人确认遇难,虽有1592人获救,但仍有近200人失踪,遇难人数仍在增加,82个临时救济营里容纳了逾8000名受难群众。
山体滑坡可以说是喀拉拉邦东部一直延伸至西高止山脉的一种地方性自然灾害,该邦的山体滑坡发生量一直稳居全印最高。
根据印度地球科学部的数据统计,2015年至2022年,全国有记录的3782次山体滑坡中就有2239次发生在喀拉拉邦。
可是仙境般的喀拉拉邦为何陷入如此困境?要是把人性也算作自然天性的话,那么在喀拉拉邦发生的一切倒是都可以推锅给“天灾”。
尽管印度环境委员会多次发出警告,但滥伐采石和森林砍伐却从未停息过,迫使喀拉拉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西高止山脉生态专家小组成员、环保主义者V.S. Vijayan说,Wayanad发生的灾难完全是“人类有意为之所造成的”。
在世界各国享有国际声誉的环境史学者Madhav Gadgil起草的西高止山生态专家小组(WGEEP)报告,早在2011年便呈递给了印度联邦环境部。
这份专家小组报告被认为对那些允许缺少全面风险评估仍在山坡上肆意开展基建工程的邦政府敲响了警钟。
报告将Wayanad风景如画的两个乡——Vythiri Mananthavady和Sultan Bathery 列为了最高等级的一级生态敏感区(ESZ-1),并要求这个区域的土地使用必须0变化。
而令人发指的是,就在距离灾难发生的Mundakkai和Chooralmal两个村庄仅2-3km处的Vythiri乡的Meppadi村,赫然属于报告中认定的喀拉拉邦18个生态敏感区之一,却与用地0变化的原则背道而驰,正深受着印度政商巨头们所谓“现代化”改造的荼毒。
专家小组曾提议,采石作业及其他污染指数在60及以上的红色行业应当在一级生态敏感区被完全禁止。
此外,那些允许采石作业的区域也应该与人类居住区保持至少100米的距离。然而,喀拉拉邦政府竟公然将安全距离直接缩短了一半,改为了50米。
结果就是,肆意泛滥的采石场和遍地开花的旅游度假村彻彻底底改变了Wayanad本来的地貌。
这一报告一旦付诸实施,可以预见很多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的经济利益必然受到冲击。
于是乎在多个邦政府的联合反对下,中央政府不仅驳回了Gadgil的报告不说,或许是为了给这个生态保护的报告瘦身,还在短短一年之后又重新任命了一个高级工作组,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ndian Space Research, ISRO)的前主席K.Kasturirangan作为领导。
果不其然,没有让这些政商巨头失望,Gadgil的专家组希望将西高止山脉范围内75%的地区划归为生态敏感区。
而K.Kasturirangan的工作组直接就给砍到了37%,即使是这样,这37%的生态敏感区还在地方政府的拖延战术下至今未收到生态保护政令的通知。
2022年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及公共卫生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50年至2018年期间,Wayanad地区62%的森林消失了,而种植园的覆盖率却实现了1800%的飙升。
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就像是世界范围内的森林破坏一样,成为了无人认领的坏小孩,又一次回到了犯罪现场。
极端的天气现象对像西高止山脉这样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精准打击,进一步加剧了这个世界八大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的生态脆弱性。
印度科钦科技大学(CUSAT)大气雷达研究高级中心的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受气候变化影响,印度西海岸的地热效应进一步加剧,降雨正变得更具对流性。
该研究中心的主任S.Abhilash说,“阿拉伯海域的变暖直接导致了深云系统的形成,这一系统会导致喀拉拉邦出现短时间内的集中降水,从而反过来增加山体滑坡发生的可能性。”
变暖的海水在热力学上使得上空的空气变得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本身就和气候变化是强相关的。
早些时候这样地热影响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印度西海岸Mangaluru北部的北Konkan降水带上。
政治游戏的牺牲品?
《国际环境研究及公共卫生杂志》的研究强调,对暴雨及其次生灾害预警不容忽视。
印度休姆生态和野生动物生物学中心通过收集Wayanad地区超过200多个地点的降水数据。
在7月29日上午9点,也就是灾难发生前的16个小时,就明确向当地政府发出过关于Mundakkai及其周边区域有发生山体滑坡的可能性的严肃预警。
该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在距离Mundakkai最近的Puthumala地区的雨量计在7月28日已记录了200mm的降水量,7月29日凌晨又记录了130mm。
根据休姆中心主任C.K.Vishnudas所述,大约600mm的连续降水就能引起山体滑坡。从7月28日算起,48小时内该地区的连续降雨量已经达到了572mm。
早在2020年休姆中心也发出过一次预警,称Mundakka地区有山体滑坡的风险。
根据这一预警当地政府组织了居民紧急避险,成功躲过一劫。然而这一次虽说当地政府部门也组织了一些紧急疏散,但不幸的是,疏散范围远远不够。
更令人尴尬的是,7月19日,联邦煤炭和矿业部部长G.Kishan Reddy在加尔各答印度地质调查局总部为新成立的国家滑坡预测中心(NLFC)揭幕。
该中心上线了一套先进的人工智能滑坡预警系统,这套系统通过整合实时降雨信息及边坡不稳定测算数据,可实时更新滑坡灾害风险清单,为当地政府提供预警信息,从而减轻山体滑坡造成的损失。
国家滑坡预测中心在Wayanad的分部同样上线了这套智能系统,然而却在本次灾难发生前,并未能如约预测到这一毁灭性的山体滑坡,更没有向当地政府部门发出有效预警。
事实上,预警是否提前有效发出成为了有争论性的焦点。联邦内政部长Amit Shah声称,预警是事故发生7天前,也就是7月23日就已经发出的,国家灾害反应部队(NDRF)当天即派出9支队伍前往喀拉拉邦进行应急响应。
而喀拉拉邦首席部长Pinarayi Vijayan却否认这一观点,说他们并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同时还引用了气象部门6月29日-30日大雨橙色预警作为反例佐证他的说法。Pinarayi Vijayan要求Amit Shah“停止玩弄政治手段”。
联邦内政部长Amit Shah,曾任印度人民党主席,从小就参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极为活跃的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者。
而在南北问题突出的印度,本就对印人党或者说对莫迪极为不爽的南部诸邦中,喀拉拉邦一直是出了名的左翼邦,在2024年大选之前都一直保持着印人党在该邦的0席位记录。
该邦的首席部长Pinarayi Vijayan,印度最大的左翼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局委员,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向来以在公开场合炮轰印人党而著称。
可是政治立场的差异和政治利益的争夺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可以凌驾于生死攸关的民生问题之上的核心出发点?现代版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炎凉世态跃然纸上。
公共服务缺失,是能力问题还是意愿问题?
除去相互指责和攻讦以外,充斥在Wayanad和其他易发生山体滑坡地区的,还有百姓心中普遍对为防止悲剧重演而组织的疏散和重新安置的忧虑。
人们面对合理的迁置补偿缺失前提下的重新安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而这一挑战恰恰是喀拉拉邦政府迟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生物学家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P.E.Easa哀叹:“我们只有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才去讨论社区保障,却往往忽视了支撑灾难管理的最基础的条件。
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喀拉拉邦有限的空间和高人口密度之间的矛盾。
因此,行之有效的灾难管理实践至关重要。”道理谁都懂,但是否选择对此采取行动又是政客们的另一层考虑了。
一场大雨,扯碎了喀拉拉邦的山石,也扯碎了印度政府政治游戏和公共服务能力的遮羞布,随之破碎的,还有底层百姓对生的希望。
本文为印度通原创作品,任何自媒体及个人均不可以以任何形式转载(包括注明出处),免费平台欲获得转载许可必须获得作者本人或者“印度通”平台授权。 任何将本文截取任何段落用于商业推广或者宣传的行径均为严重的侵权违法行为,均按侵权处理,追究法律责任。
>> 热文索引 <<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广东
广东